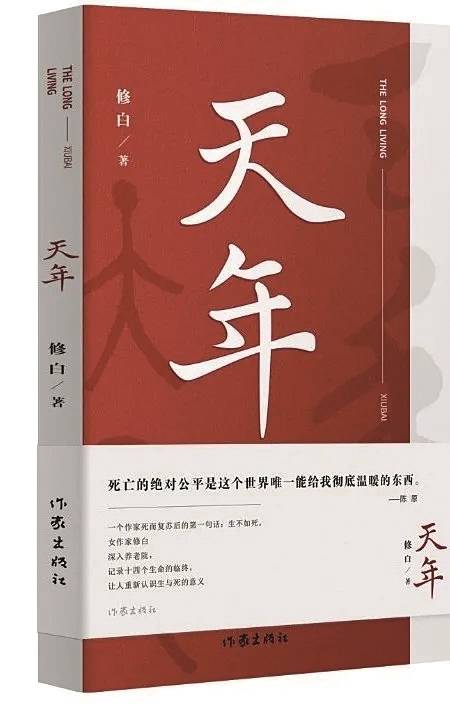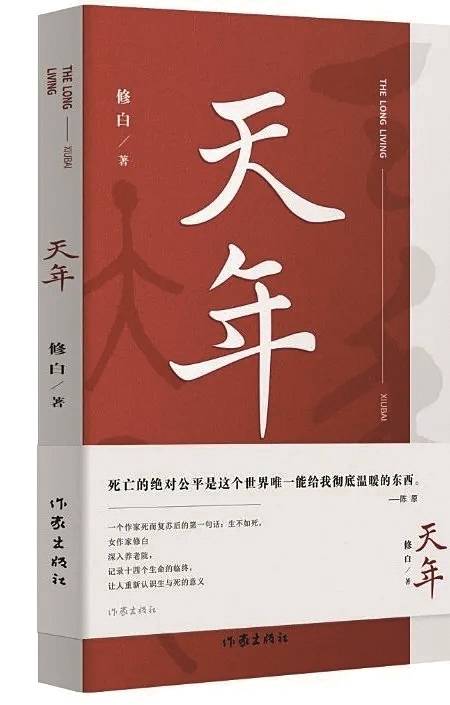
《天年》
能够颐养天年、尽可能愉快地度过人生晚境,体面地迎接死亡,是每个中国人的理想。近日,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优秀成果之一、江苏作家修白的纪实文学《天年》出版,修白用三年多时间,深入多家养老院观察体验,采访、亲历、记录了十位老人走向人生终点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老人的“最后一程”走得并不宁静,“天年”一词亦构成了对现实的微妙反讽。
由沉重的“养老”“死亡”话题出发,修白呼唤重构一种“哺育与反哺”的健康家庭机制、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和爱,以及更加开阔、坦然的生死观。
《天年》首先写出了老人之“困”。比如,有老人因为丧失了行动能力,晚上睡觉时只能保持固定的姿势,等到起床时一条胳膊已经被压得像乌骨鸡一般;有的老人遭遇过部分不负责任的护工的粗暴对待,被摔倒在床上,或被呵斥着迅速扒饭。子女们的遗产之争也时常在老人的病榻前上演,书中一位老太太不堪孙辈索要财产时的侮辱愤而跳楼自杀。甚至,个别家人有时也会委婉或直接地向垂暮之人表达希望他早日离去的意思,闵爷爷的老伴就时常在他耳边念叨,“你不要把我拖死”……
在省作协举办的“修白纪实文学《天年》研讨会”上,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汪政忆起不久前探望一位生病老人时的情形:他看到老人的轮椅周围摆满了凌乱的物品,正纳闷为什么不请护工帮忙收拾,老人解释,这些生活物品就是要放到她伸手可及的地方,换言之,轮椅周围不足一米的范围,就是她全部的生活半径。但更令汪政感慨的还是临终老人们在社会学意义上时时遭到的漠视——他们既谈不上参与社会生活、表达自我,也无力唤起周围人对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爱。 这正是《天年》所揭示的老年人晚景生活中的“隐秘角落”。
当然,作品择取的案例较为极端,远不足以反映普遍的老年生活,但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部分老年人在生理性死亡前就已经遭受的“社会性死亡”。这样读者也就理解了,书中夏洁为何特意当着护工的面把父亲当作宝贝一样心疼,甚至优雅地用英语和父亲交流,就是希望能够在社会学意义上为行将就木的父亲赢得一份尊重和关注。
《天年》更揭示了“死”如何与“生”相纠缠。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瞬间,如何勇敢地迎向这一刻,所依赖的是个体一生的精神积淀和“哺育与反哺”的健康家庭机制,而一些家庭冷漠的夫妻关系、粗暴的亲子相处模式,实际上为老人的凄凉晚景埋下了恶因。苏州大学青年教师李一观察到,一些年轻人习惯于功利化地对待亲情,将父母为自己买房、带娃视作获得赡养的“议价筹码”,流露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
珍视生命、尊重生命并不等同于“过度医疗”。修白观察到,在中国,过度医疗常源于社会对老人子女的道德绑架,不计代价换取老人的低质量生存成为了一种“伦理正确”—— “我父亲重病时,我在绝望之中拨通了某位医学专家的电话,我渴望减轻父亲的痛苦,专家却奉劝我一定要把父亲送到大医院继续检查,否则就是和整个社会习俗对抗。但我清楚地知道,父亲已经不可能好转起来,于是我一边尽可能地减轻父亲的痛苦,一边盼望他睡过去——放弃治疗并不是不爱。相反,正是因为那么深地爱他、怜悯他,才会那么痛地希望他早点离开……”修白说。
人的死亡之路荆棘丛生,修白这样总结。从照顾父亲直至他逝世的这段经历中,她洞悉了一个社会里遭到“异化”的生死观:死亡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却讳谈或千方百计躲避。其实,讨论死亡就是讨论生活的态度,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才是向死而生的积极态度。修白还希望,人们能够“更宽阔”地去爱,一如她在为父亲恸哭时,也是在为所有苦难的、布满荆棘的死亡之路而恸哭;给父亲喂饭时顺便喂邻床老人一口,也是生而为人所应有的悲悯。
本报记者 冯圆芳